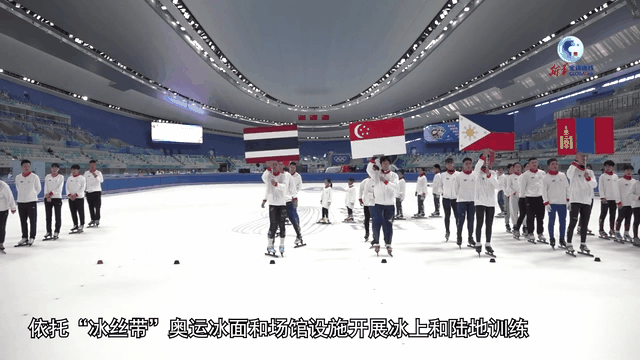黃河上游,山地、高原、平川、河谷錯雜分布的廣袤地帶,有這樣一種震撼心靈的“大地飛歌”。
這是一種名為“花兒”的民歌:它的“花瓣”形態各異、色澤不一,圍繞著定海神針般的文化之“蕊”,在你一句、我一句的漫唱中,生出共情的美。
它是“大西北之魂”,印刻著千百年來莽原的滄桑變遷;是“活著的《詩經》”,閃爍著中華民族一脈相承的文化訊號;是平凡人寫給生活的情詩;是民族間交往互通、互助互信的信箋。
它艷而不俗,活色生香,抵住了歷史的滔滔巨浪,至今仍卷攜古曲新韻,躍動在人們的心尖上。

6月13日,在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松鳴巖景區,花兒愛好者表演花兒。新華社記者 范培珅 攝
解碼中華文明的“密鑰”
聽到“關關雎鳩,在河之洲”,人們總能對答如流,好像有顆生長在血脈深處的種子,正在千年前的河畔隨風搖擺,生根發芽。
花兒似有這樣穿越時空、聯結情感的魔力。它生長在西北,這里自古以來就是多元文化相映共生的沃土。絲綢之路和唐蕃古道攜萬千車馬、人流奔騰而過,漢、回、藏、撒拉、東鄉等十多個民族來往駐足、雜居錯處。
幾千年間,農耕文化和草原文化不斷包容、互通,人們把各自的文化特色融進歌喉和唱詞,生出這種富有詩意的溝通訣竅。口耳相傳中,兼容的花兒,在甘、青、寧、新等多個省區遍地盛開。
花兒繼承著西北的風土人情。它外表粗獷,吸收了羌、藏等民族高亢嘹亮的曲風,每個音節都能穿透莽原朔風,直抵心靈深處;它內心“水靈”,語言上使用流通面廣、表達豐富的漢語方言,打破了地域、民族、年齡等限制,將共鳴推向高峰。
“尕妹是園里的白牡丹,開下的艷,根扎在阿哥的心上……”愛情是花兒永恒的主題,除了花卉,日月星辰、山川河流、草木蟲魚等常見事物,都能以信手拈來的比喻、興懷,插上抒情之“翅”。《詩經》中的修辭,始終流淌在西北人連綿不斷的歌聲里,從未走遠。
看到“雪白的鴿子從水面上飛來”,就有“阿哥連尕妹一對的鴿子,尾巴上連了惹人的哨子”;看到“白牡丹白者耀人哩,紅牡丹紅者破哩”,就有“尕妹妹傍個有人哩,沒人是我坐哩”……由景到人的興懷,即使直白,卻掩蓋不了中華民族文學思維的異曲同工。
一曲花兒,就能解碼積淀千年、一以貫之的文化精魂。
隨著廣泛傳播,花兒衍生出河湟花兒、洮岷花兒、六盤山花兒等不同種類,曲令數量也不斷飆升,以地名、人物、動物、花卉,甚至“大眼睛”“憨墩墩”等形象特征、“咿呀咿”等語氣襯詞命名的曲令大量涌現。據不完全統計,僅在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一帶,就有300多首花兒曲令仍在流傳。
對于新鮮的文化現象,文人墨客總不缺席。在他們的詩文里,田間地頭“漫聞花兒斷續長”的老夫、村女,大膽地將花兒帶入廟會活動,開創了“老僧新開浴佛會,八千游女唱牡丹”的盛況。
后來,花兒擁有了專屬的競唱會場,“粉絲”群體不斷壯大。在甘、青等地,傳統的花兒會場達100多處,參與群眾從數萬人到數十萬人不等。
就這樣,不同的花兒相映共生、水乳交融。花兒會場里,人們懷著對生活的美好祈愿,或高聲對唱,或助威吶喊,或延續著“維士與女,伊其將謔,贈之以芍藥”的古老傳統。
不知不覺間,綿延幾千年的中華文化密碼完成又一次傳承和續寫。
平凡人的質樸哲學
千百年過去,花兒仍是西北人生活中一份鮮艷的鄉愁。
在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松鳴巖景區一年一度的花兒大會上,來自多個省份的民歌演唱者齊聚山野,和十里八鄉的男女老少同歌共舞。雖然閃爍著不同文化的印記,但只要漫一句“左面的黃河么噢喲”,臉上就都雀躍起同一種興奮、歡快、沉醉的表情。
什么給了花兒如此巨大的魔力,答案在山頭、田間和河畔。
田里干活的人,閑下來對著遼闊的麥田吼一句,“莊稼離不開好種哈選,好收成它就是本錢”,手上有勁了;河上擺渡的人,迎著大浪激起的水花扯一嗓,“雙手搖起了槳竿子,好像是天空里的鴿子”,身上輕快了;修渠、放牛、煮酒、烙饃的男女老少,把手頭的活計、嘴邊的話一股腦倒出來,心頭舒坦了。
花兒是生產生活的“背景樂”,是解壓打氣的“號子”,是勞動人民唱給別人、唱給自己的盼頭,生長在遼闊厚實的土地上。
什么給了花兒豐厚的滋養,答案在“阿哥”和“尕妹”里。
傳說,西北的某個村莊立有一塊“班輩石”,花兒會召開之際,一群年輕人高唱花兒將石頭搬倒,如釋重負地奔向遠地。故事雖已無法考據,但花兒對封建禮教的反抗,對心靈的解放卻真實存在。
“玫瑰花好看你莫要摘,摘是刺刺扎呢。花兒好聽你莫要亂唱,莊子里唱是老漢家罵呢。”60歲的花兒演唱家雷蘭芳記得,曾經很長一段時間,花兒都被老一輩人視為離經叛道的“野曲”。
“情歌嘛,上不了臺面,但心上的話,不唱怎么由得自家?”下地干活時,一個莊子的人總是忍不住漫起花兒。此起彼伏的歌聲、朗朗上口的音調、熱烈的唱詞,敲開了大山深處的雷蘭芳的心。
小時候,她看著爸媽吹羌笛、漫花兒,把感情藏在“阿哥是山上的金絲蓮,尕妹是泉邊的水仙”里;長大后,她也唱著“男子的二十呀女十八,新婚姻政策上合法”,大膽追求自己的愛情和生活。
生活越貧瘠,心靈越熱烈。那些曾被封建時代壓抑著的自由、年輕、美好的情感,借著花兒躍動,也借著花兒永遠盛開。
“花兒皇后”蘇平形容花兒是老百姓“護心的油”。“有次表演時下大雨,老鄉們就淋雨站著聽,怎么這么癡迷?這是心里的信仰。有次村里沒舞臺,我去一家人院里唱,樹上、墻頭、門里門外全是各民族的老爺爺、老奶奶,怎么這么大‘癮’?這是他們年輕的心。”
“花兒為什么能‘紅’到人心里頭?因為它不只是情歌,還是關于真善美的無限希冀和想象。”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政縣文旅產業發展中心主任蔣勝利說,花兒是“勸化人心的‘少年’”,是來自平凡人最直白、溫柔的表達。“它是歌,也是生長在民間的質樸哲學。”
多元一體的文化“基因”
對47歲的藏族群眾李梅來說,花兒一響,心門就開了。“我覺得最好聽的花兒,是媽媽站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,帶著藏腔‘漫’出來的。它有青草、牛羊的味道,有我從小到大最美的回憶。”
李梅來自青海省西寧市湟源縣,地處青海湖東岸、日月山東麓,漢、藏、回、蒙、土等十多個民族錯雜居住。湟水河上游的水源,滋養著生活的恬靜。各具特色的花兒,則讓精神世界更加豐厚多彩。
“在我老家,大家喜歡把藏族悠長、高亢的曲風揉進花兒,聽起來高音更加婉轉動聽。”李梅說,花兒是出了名的“十唱九不同”,每個地區的人們都能在唱腔、襯詞上做出改變,漫出自己的風格。
走進百“花”齊放的“大觀園”,只聽得有的曲令激越豪放,“上去了高山望平川,平川里有一朵牡丹”讓人豁然開朗;有的曲令剛直流暢,“花花的麻雀們連聲地叫,心急著眼皮們跳了”惹得心跳加快。抑或是遼闊悲壯、纏綿跳蕩、柔美抒情……
一首首各具特色的花兒,讓不同區域各族群眾的性格有了鮮活的“傳聲筒”,也讓人們有了傳承文化、表達自我的窗口。
在西北一些多民族聚居地區,長期的互動交流,催生了漢語、少數民族語言混用的“風攪雪”花兒。
如“天上的云彩黑下了,尕加得忽拉五繞嚇;想起花兒哭下了,思格里杜五郭那谷勒嚇。”二四句是土族語言的音譯,意為“地上的雨點大了,記起說下的話了”。唱完第一遍,人們還要反過來把一三句用土族語,二四句用漢語再唱一遍,最后全用土族語唱一遍。
除了句與句交替,一些“風攪雪”花兒還有詞對詞翻譯。各族群眾想方設法“風雪共舞”,只為打破“語言壁”,實現“溝通自由”。
如今,越來越多人將花兒改為徹頭徹尾的民族風。來自新疆的哈薩克族歌手加爾肯別克就喜歡彈著冬不拉唱“哈薩克花兒”。
“花兒詞曲靈活,加工空間大,我把一些曲目翻譯成哈薩克語,伴奏上略微改良,就有了哈薩克族歡快、熱烈的風格,很受歡迎。”加爾肯別克覺得,花兒兼具個性和共性,是民族融合的“結晶”。
“在青海,經常會有回族村、藏族村、土族村比賽著唱花兒,這就像一種‘共通語’,你一唱,所有人都能進入共同的狀態,哪怕聽不懂,也能跟著調子一起哼。”青海省民間文藝家協會副秘書長楊韶鵬說。
“先栽葫蘆后搭架,花開了葫蘆吊下。各族團結的力量大,石山上開一朵紅花。”正如這首花兒中唱到的,不知不覺間,花兒已讓各族人民心手相牽,走進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共同的精神家園。
奔上大道的駿馬
如今,花兒已飛出草原、山坳,走向更大的世界。
2006年,花兒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;2009年,花兒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作為珍貴的“世界之聲”,花兒的傳承、融合、創新步調不斷加快。
在甘肅、青海、寧夏等地,花兒會不再局限于小范圍山野競唱,而是演變為集展演、考察、研討于一體的綜合性活動。在2023中國花兒大會上,全國各地的歌手帶來多元化的民歌展演。同時,專家學者、院校團隊走村入寨考察探討,為花兒發展建言獻策。
花兒的傳承保護也開始“有法可依”。2016年以來,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、天水市張家川回族自治縣相繼出臺花兒保護傳承條例,規定劃撥專項資金,用于花兒搶救、記錄、調查、整理,花兒原始資料、實物征集、保存,花兒詞曲研究、成果和刊物的出版發行等方面。
越來越多散落民間的演唱家被“發掘”為花兒的代表性傳承人,他們在政府支持下整編花兒詞曲,參與培訓、考察。一些傳承人還開辦工作室帶徒,在民歌展演、節目、課堂中推廣花兒。
“為了滿足現代的審美需求,各地還在推進花兒的舞臺化。”蔣勝利說,臨夏回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劇團就創排了多部融合音樂劇、現代歌曲、現代音樂元素的花兒舞臺劇。其中,《布楞溝的春天》《幸福像花兒一樣》等劇目受到國內戲劇專家及群眾的好評。
今年,臨夏花兒歷史博覽傳承中心開工建設。“我致力于收集花兒資料,先后給臨夏州博物館捐了70多箱書籍、報刊、光盤、照片等,現在有了專門的‘博物館’,花兒的前世今生就能更加清晰地娓娓道來。”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花兒文化專業委員會副主任郭正清說。
當然,作為一門略顯“小眾”的藝術,花兒的傳承仍面臨一些困難。“目前,花兒歌手趨于老齡化,傳承人青黃不接。我們正試圖通過政策支持‘兩步走’,在推動原生態區域內‘師徒制’傳承良性運轉的同時,培養更多科班出身的專業歌手。”蔣勝利說。
“花兒的歌詞是方言,很多年輕人聽不懂,難以融入。”來自青海的“90后”花兒歌手陳有定說,自己曾嘗試用更流行的語匯豐富花兒唱詞,受到了很多同學的歡迎。“花兒本身就是包容的藝術,用年輕人喜歡的方式作詞、伴奏,會迸發新的生命。”
花兒要創新,但不能傷“根”,這是藝術家們共同的默契。“新時代,花兒需要在表現形式上更加藝術化,但一定不能背離其原生態的內核,不能打亂旋律走向,脫離人民。”蘇平說。
一匹駿馬從草原奔上大道,必然要改換發力方式和步調,但它最為原始、本真、野性的美,仍將帶給人們永恒的震蕩,花兒亦如是。(記者王紫軒 胡偉杰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