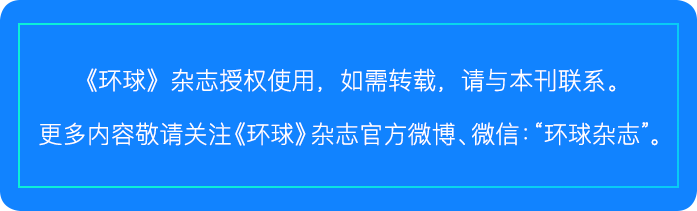看海

亨利·摩爾畫(局部)
文/《環球》雜志記者?楊春雪
編輯/胡艷芬
今年在北京遇見博物館的《遇見印象派——莫奈、雷諾阿與諾曼底大師真跡展》上,以及國家大劇院的展館里,遇見了一些關于海的畫作。這開啟了我浪跡世界時,關于海的記憶。
美國詩人羅伯特·弗羅斯特有一首詩,題目是《既不深也不遠》,講的是人們在海邊總是習慣于凝望大海。然而,他們既望不了多遠,又望不到多深。
“但是這豈曾阻止/他們向大海凝神?”他寫道。妙極了,一語道出看海人的感受。
然而詩人始終沒有解答一個疑問:既望不遠又望不深的人們,在看海時,究竟在看什么?
海的波浪
“然而海,以及波的羅列。”在臺灣詩人林亨泰筆下,大海被簡化成波浪的羅列,一種橫在天地間的線條紋飾,無限循環,通達天地。而在廣袤陸地上長大的我們,則可通過岸邊散落的波浪觸摸海的脈搏,感知海的善變——溫柔時逐人衣裙,慍怒時鞭笞岸礁。
所以看海是一種緣分。各處的海留給人的印象不同,因有天氣、時間等變量。比如,墨西哥坎昆的海是乖戾的,那是因為我碰巧在暴風雨前遇見它,險些被吞卷;而美國洛杉磯圣莫妮卡的海卻是溫婉的,那時伴著時差帶來的困意,迎著徐徐吹拂的海風,啁啾的鳥鳴,竟仿佛聽到催眠曲的余韻。
不過,每個人對海浪都有各自的偏愛。我偏愛大浪的刺激,記得中學時在青島,擇一個漲潮的大風天下海,目視高聳的浪墻壓近,齜出巨大的皓齒。這時倘若縱身一躍就會被浪拍中,但若迅速鉆入浪底,便躲過一劫。再高的浪,內里卻是平靜的。待回首一瞥,浪已撞碎在岸邊。住在海邊的人總對大浪抱有執念,我認識一位熱愛冬泳的青島“搏浪者”,他總喜歡在臺風將至時下海,體味與海浪搏擊命懸一線的狂喜。
最近看不少關于海的畫展,發現畫家對海浪尤其偏愛。英國畫家威廉·透納筆下的海總是巨浪滔天,令人感喟生命何其渺小;法國畫家歐仁·布丹畫的海多是微風細浪,溫柔恬靜,觀者想漫步畫中;法國畫家古斯塔夫·庫爾貝的海則帶著些哲思——平靜的海面蘊藏著暴力,風暴中的海卻有平靜的一面;至于英國藝術家亨利·摩爾,心無旁騖的他專心研究波浪的準確塑形,所以他的海景畫里鮮有船只或人物,只有詩句中那無限的“波的羅列”。
海的顏色
比起波浪,更善變的是顏色。海的顏色太多了,每時每刻都不同,光線的強烈、大氣的透明度都會影響人們對海的顏色的判斷和印象。陰天的海昏黃,晴天的海藍澈,與日月起落相伴的海,最唯美。
比起看日出須早起的刻意,海邊日落的隨意更讓人心儀。日落時分的海,就像英國作家石黑一雄在《長日將盡》里描繪的場景——海面上天空變成淺紅,仍有不少天光尚存,海邊碼頭上燈光亮起來,海邊漫步的人群歡呼雀躍繼而駐足觀望,華燈初上,感受“傍晚是一天當中最美好的時光”。

厄瓜多爾加拉帕戈斯群島上的海邊魚市
記得行進在臺灣墾丁的白沙灣海灘時,我在電瓶車后視鏡里看過一場極美的落日;在墨西哥阿卡普爾科海灘,我目睹了一枚紅日完整墜海的過程;在厄瓜多爾加拉帕戈斯群島,我在半山腰觀賞了軍艦鳥歸巢時的落日。相信很多海邊落日收集者都會銘記那個時刻動人心魄的美,穿越記憶的閘門永留心底。
至于月光下的海,單是美國詩人艾米莉·狄金森《月亮離大海十分遙遠》中的琥珀色意象,就足以抒發所有浪漫:月亮離大海十分遙遠——/而她用琥珀色手——/牽引他,像牽著聽話的孩子——/沿規定的沙灘走——
海的邊界
相比波浪和顏色的多變,海岸似乎是較為恒久的事物。但從更廣的范圍來看,海岸景觀亦是變換的。
最松軟的海岸是沙灘。我在拉美時,每涉足一處海灘,總會收集一小捧沙子,裝到一個小瓶子里,做上標記。閑來玩味這些細小的顆粒,仿佛小小瓶中盛著一整片海灘:墨西哥韋拉克魯斯的沙子黑而細,與安提瓜和巴布達的白沙恰似孿生的一對,好像黑白胡椒粉兩種調味料。而古巴巴拉德羅的沙子色澤最好,是其中摻了細碎貝殼的緣故。
更常見的是礁石的海岸。礁石是守護陸地的侍衛,大概肩負著破浪的使命,所以每一塊石頭生來都是銳利的。我見過最猙獰的礁石海岸是在臺灣墾丁的龍坑,那些礁石果如其名,像極了遠古巨獸的遺骨化石。立于其上,總忍不住思索“水與石孰剛孰柔”這個恒久的話題。記得前年秋,青島海邊有塊叫做“石老人”的礁石在一場風暴中轟然碎了。除了惋惜一段古老傳說,更令人感慨的是,在時間面前,世上本沒有什么絕對堅硬的事物。
還有海岸的高山,青島嶗山便是一處,登山觀海,云里霧里自帶一種憑虛御風的仙氣;還有如英國多佛的懸崖海岸,那一抹亮白令人心馳神往。
不同的海岸線自有不同的美,但我們至多只能在海的一邊眺望,而大海卻還有另外一個邊界——那是與天相交的界線。那恐怕是我們永遠無法企及的地方。
海的生命
關于海的生命,我所見過最壯觀的莫過于加拉帕戈斯群島了,那是啟發達爾文寫《進化論》的地方。每日晨起散步至海邊魚市,看漁船滿載而歸,漁夫上岸處理魚肉。好戲此時上演——海豹撒嬌蹭漁夫衣襟求食,鵜鶘在一旁覬覦,軍艦鳥不時在空中偷襲,其他不知名的小海鳥則在角落撿漏。置身于這些美好的生命中,會感到人類也不比一只海鳥優越什么。
若不安于岸上,也可以潛入水中。很多人來加拉帕戈斯是為了深潛,一睹錘頭鯊游弋的盛況。當時只是浮潛幾日,隔潛水鏡觀賞小鯊魚、海龜、海馬以及各色小魚,已頗為滿足。
即使隨便走近一處海灘,若趁落潮時仔細探尋,也定能發現不少“遺珍散珠”。我常到青島鰲山衛附近無人的海灘上欣賞螃蟹的“天書”。只見密密麻麻的小沙球從螃蟹藏身的洞口輻射開來,連成片,俯瞰就像是一幅幅用沙粒繪制的精美壁畫。這是螃蟹進食留下的沙球,進食路線不一,沙球的排列則不同,構成的圖案也迥異,甚至很容易從中辨認出花朵和人物。
還有海鷗,常常是在日落時分,起潮的海面上停滿一整個海灣,遠看像是一只只疊好的白紙船。撒一把面包,它們會紛紛飛來爭搶,被這些輕盈的生靈圍裹,人會產生一種羽化飛升的暈眩感。
就連最不起眼處也藏著驚喜。譬如,礁石坑洼處一小汪海水里,幾條小魚在焦急等待著被大海接回;礁石縫里,偶爾會有幾只膽小的螃蟹探出頭,或者匆匆閃過;泥沙多的海灘下面筑有蟶子和蛤蜊的暗道,倘帶上馬扎,一袋鹽,一個鐵鏟和一個水桶,就能在沙灘上消磨一下午的時光,直到被海水趕回陸地,運氣好時可以收獲滿桶的美味。
海,令人著迷。美國作家赫爾曼·梅爾維爾在《白鯨》里這樣寫,“海有一種魔力,總能把人們吸引到大陸的邊緣”。或許就是這個原因吧,我每隔一段時間,必要看看海。仿佛覺得自己就是大海潮汐輪回時遺漏的一滴,離開久了就要回家看看。好在如今從北京到青島的高鐵快極了,比當年從墨西哥城一路下高原輾轉到阿卡普爾科看海,實在方便太多。
那么,我們看海時究竟在看什么呢?海的波浪、顏色、邊界以及生命……以上答案可能都是,又可能都不是。
或許,我們看的是內心的海,一片快樂的、憂郁的、浪漫的、沉思的大海。
記得常去看看海。